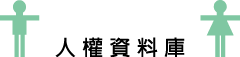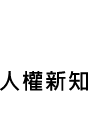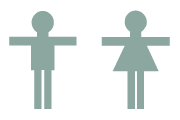|
|
||||||||||||||||||||||||||||||||||||||||||||||||||||||||||||||||||||||||||||
| 人權學堂 ∣Human Rights Learning Studio 位置:高雄捷運O5/R10美麗島穹頂大廳方向往出口9 Position: Kaohsiung MRT 05/R10 Formosa Boulevard Hall Exit 9 郵寄地址:81249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北路436號 Address: No. 436, Daye North Rd. Siaogang Dist., Kaohsiung City 81249, Taiwan 電話Tel:886-7-2357559∣傳真Fax:886-7-2351129 Email: hr-learning@ouk.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