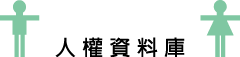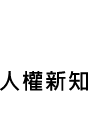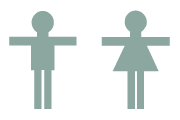抗議“愛滋孤兒”讀書 不是文明社會應有之舉 抗議“愛滋孤兒”讀書 不是文明社會應有之舉
阿龍是廣西省柳州市牛車坪村的一名愛滋孤兒,阿龍6歲,父母均因愛滋病去世。今年9月,阿龍的奶奶送阿龍去學校讀一年級,有家長得知後,向學校寫聯名信表示抗議,這些反對聲最終使得阿龍無法入學。
盡管社會各個方面都給廣西愛滋孤兒給予了關注,但是,其就讀普通小學遭家長聯名抗議的事實再次告訴我們,在當前的語境中,愛滋病不僅僅是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疾病,而是一個被社會加以定義的問題——已經被高度道德化。
我們不但可以從科學上證明“校園中發生血液傳播的概率並不高”,也有事實證明愛滋病孩子在普通的學校生活、學習,並沒有給身邊的同學老師造成任何影響,但是,這一切都很難讓家長們放心,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心理上難以接受。這在筆者看來,就是對愛滋病孩子進行道德審判的必然結果。
對於愛滋病,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兩種觀點,一種是把愛滋病感染者視為“道德敗壞者咎由自取”。另一種觀點是防治愛滋病主要是為了保障個人的健康權,健康權是一種基本人權,體現出醫療公平等。這種思維的內在邏輯是人首先是社會的主人,因此人的權利的實現程度是評價防治愛滋病工作的成效與社會發展進程的根本指標。但是,廣西愛滋孤兒就讀普通小學遭家長聯名抗議告訴我們,對愛滋感染者的歧視已經刻板化。
愛滋病不僅僅是一種疾病,更是一個社會問題,最終需要依靠科學戰勝它,需要我們從生活、制度和文明的根源上戰勝它。廣西愛滋孤兒就讀普通小學遭家長聯名抗議是由歧視帶來的社會排斥,這不利於社會文明和社會進步。因此,需集中政府、社會、民眾三方面的力量,加以解決。
筆者以為,我們必須明確愛滋病只是一種疾病,愛滋病感染者僅僅是病人。防治愛滋病工作必須反對任何形式的對於愛滋病感染者的歧視,因為人人生而平等。我們知道,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愛滋病的危害其實並不是疾病本身,而是它所帶來的社會恐慌,因為愛滋病雖然屬於慢性傳染病,但是它卻被賦予了太多的道德含義,甚至某些旨在預防愛滋病的宣傳教育也在不自覺地強化著這種道德含義。這加劇了愛滋病恐慌,造成了社會歧視。
因此,面對廣西愛滋孤兒就讀普通小學遭家長聯名抗議,就需要理性地拋棄高度道德化對待愛滋病的現實,不應對之進行道德審判,這是消除歧視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排斥的點。。
(2010-11-30/新華網)
|